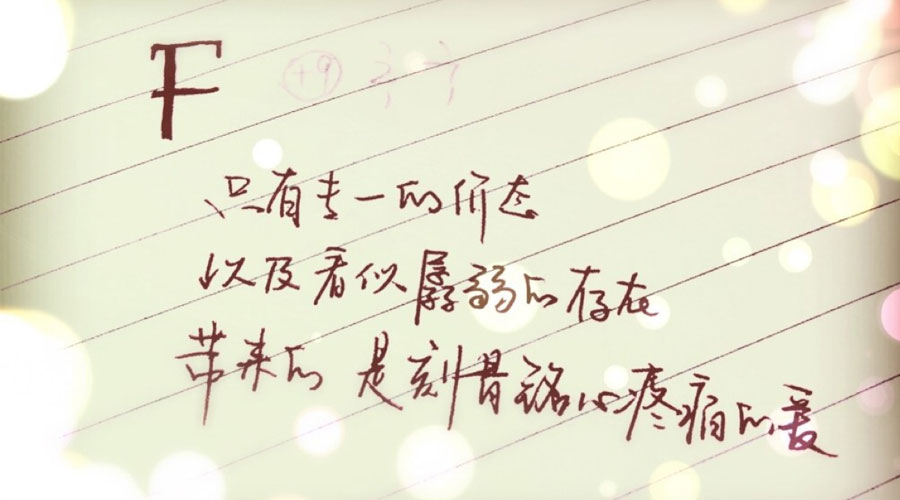快乐的感觉是一种自我体验,当然,也要有社会的评价。如果你自己的体验和社会的评价能平衡,那你的快乐分值就会比较高。比如,你认为自己很牛,大家也吹捧你很牛,这就说明你的自我体验和社会对你的评价是一致的。而像唐骏,他自己认为他的成功可以复制,但大家发现他的学历可以粘贴,这就说明他的自我评价和社会对他的评价出现了误差。人生其实是非常公平的,在每个阶段,你得到的快乐都来自于自我的评价和社会的评价。极度爱慕虚荣的人内心是极其虚弱的,他的自我评价系统很弱,他完全靠社会对虚荣的评价系统来支撑自己。外重者而内荏,所谓外重者,就是特别在意外在形式的人,比如一个人出门带五个保镖,八辆汽车跟着,吆五喝六的。内荏,就是内心胆怯、恐惧。也就是说,如果你特别在意外在的东西,比如特别在意别人怎么吹捧你,你不是博士,非要让人家说你是博士,就说明你的内心其实是很懦弱的。
所以,要有理想和信念,也就是说,要建立内在的价值系统和自我肯定系统,同时要获得一点儿成功。获得一点儿成功,外部就会给你一点儿评价,就会鼓励你、鞭策你,强化你的自我评价系统。如此,这两个系统就能保持平衡,你就能一直很快乐。如果只有社会的高度评价,你内心完全不够自信,就会出现这个门、那个门的笑话。相反,如果你只相信自己,完全不在意别人怎么看,那你就可能走向极端。所以,一个健全的人,其内在的评价系统和外在的评价系统要保持平衡。
对80后来说,在刚进入社会的时候,大部分人都是要靠自我评价的,因为你刚进入社会,社会还没有建立起对你的评价。我给大家讲个故事。我20多岁的时候,也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热血澎湃,想干很多事情。有一天,一个很大的领导找我谈话。他说,听说你思想很活跃,我要跟你谈谈。领导要找我谈话,这事儿多了不起啊,进去以后我就开始说,说了大概一个小时。最后,这个领导说了两句话,从此我就踏实了。他说:第一,你说了这么多社会问题、这么多现象,我告诉你,你知道,我比你还知道,因为我是领导,我看到的信息、听到的信息比你多。第二,你着急,我比你还着急,因为我是领导,出了问题,我遭受的损失比你大得多。所以,不需要你教我怎么干,你跟着我干就完了。我一想,这个逻辑也对啊。
后来我明白了,在二三十岁的时候,想得到很多的社会评价是比较难的。在这个阶段,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。比如我想做一件事,我是偏执狂,我就要去做,不管别人怎么说,因为这时候社会不可能马上承认你。等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,你的机会就变多了,因为社会是被四五十岁的人控制着的。那时候,我在机关里是年龄最小的,我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干不了,找谁都是老爷爷,年龄大的人根本不理我。今天我发现,我们同学里什么人都有,有做生意的,有当博导的,有当部长的,不管什么事,只要我打个电话,都能找到相应的人咨询。所以,在20多岁刚进入社会的时候,你扮演的是一个候补队员的角色,甚至可能连候补队员都不是,只是一个足球爱好者。到了30岁, 你就混成了一个候补队员,到了40岁,就差不多可以上场踢球了。
在20多岁这个阶段,怎样才能快意人生?就是用理想来鼓舞自己,用时间来检验自己,用些许成功来安慰自己。你只会有些许成功,不会有很大的成功。当然,有的人在20多岁的时候已经小有成就了,比如丁磊、李彦宏,但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。等你熬到三四十岁的时候,你就开始进入另一种快意人生的状态。大家知道,王石60岁的时候又去爬珠峰了,爬珠峰除了要有毅力,还要有很多其他条件。我记得他第一次爬珠峰的时候,因为经费不够,找朋友集资,那时候他40多岁。到了50 岁、60岁的时候,他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也就是说,在20多岁的时候,你获得的快意并不是人生峰值上的那种快意,男人的人生峰值应该在45~55岁。在20多岁的时候,你有时间、有未来、有理想、有健康的身体,你不怕失败,你可以做无数次的尝试,等待最后那一次的成功。有人讲过一句话,他说年轻人吃苦不叫吃苦,叫有福气,因为你有选择的机会,有失败的资本。老了以后吃苦才真叫吃苦,比如你到了60岁,贫病交加,这才是真苦。在20多岁这个年龄段,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目标,不要怀疑自己的未来,而且要坚信时间是站在你这一边的,这样,你就可以快意人生。
分类: 暖文章
暖文章
谁在悄悄等你回信
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欣怡。
欣怡独身到33岁时,父母再也扛不住了,开始催婚。
这次催婚的阵势很大,好像不给他们个交代就过不去了。欣怡盘点了内心,发现自己也不是绝对的独身主义者,索性开始听父母的安排相亲。
在多场相亲后,算是锁定了一个目标。这个男人叫浩,有趣的是,浩其实是欣怡的小学同学,在四年级时转学,所以他们的相亲等于一场同学聚会。
重新续上的同学情,使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,鉴于两人年龄都不小了,很快就开始谈婚论嫁。
这时问题出现了,浩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,而欣怡在家乡也有稳定的工作。如果结婚,一方必须舍弃现有的生活,到对方的城市去。
为了爱情,欣怡决定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,结婚后跟随浩去北京发展。
一切准备就绪,可在这时上帝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欣怡的父亲得了癌症,一下子卧倒在床。在没确诊之前,医生的结论并不乐观,如果是恶性肿瘤,老人最多还能活两年。
像欣怡这样的独生子女,这时离开父亲是不可能的。于是她决定先留在家里照顾父亲,两年后再随浩去北京。如果父亲没事,不出一年,她和浩也就能团聚了。
这个想法该怎样告诉男友?欣怡很犯难。毕竟是一件需要对方理解的事情,直接说出来会不会显得很冒失?
想来想去,欣怡选择发短信告诉浩。这条短信写得很长,删改了多次,直到她认为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,而且也不显得越俎代庖。
然后,她开始等待。这种等待简直度日如年,她也难免有点儿焦急。
足足等了两天,答复没有来。
第三天晚上,在QQ上见到浩,两人又闲聊了几句。浩没提起那件事,就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。
以后几天,她还能在网上见到浩,两人仍聊着各种话题。对那天的短信,浩却一直只字不提。
浩的沉默给欣怡出了个难题,心想他是没接到短信,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,或者,他不提就是一种回答?
为了求证浩的想法,欣怡去了趟北京,出了机场就打车直奔浩的公司。浩的公司在一座写字楼的23层,公司内部的玻璃墙上悬挂着百叶窗,透过百叶窗的小小缝隙,可以观察到浩的一切。
欣怡看见坐在办公室里的浩,灵机一动。她决定先不去找浩,而是拿出手机,把之前的短信又发了一遍。
然后,欣怡伸长了脖子,默默地注视着浩。她看见,埋头在电脑前工作的浩,听到手机的震动后下意识地把头偏向了手机,拿起后扫了一眼短信,微微地发了会儿呆,手指停在手机上有几秒钟的迟疑,然后就放弃了。最后,他把手机干脆扔进了抽屉,重又回头看着电脑。
那一瞬间,欣怡知道自己没必要当面求证了。一扭头,在距离浩不足10米的地方,离开了他。
在北京街头乱转了半天,那种异乡异客的落寞感加剧了失恋的痛感,她决定买当天的火车票,马上回家。
因为来得仓促,钱带的不多,她买了一张慢车车票,这种火车从北京到西安要走20个小时。
于是欣怡就有了一段在她的生命中最难熬的旅程。坐在人员繁杂、充斥着方便面味道的硬座车厢里,欣怡饿得眼冒金星,每一种食物的气味都提示着她胃的虚空。
到站后,欣怡下了火车,来到自家楼下的面馆前。当那种亲切的味道从面馆里传出来时,欣怡突然就释怀了。
她发现自己也不那么爱浩,她失去爱情的痛楚都盖不住饥饿时见到一碗面的欢快。
后来,父亲的肿瘤被确诊为良性,她和浩回到朋友的状态,偶尔在QQ上遇见,聊两句工作和生活。
她说她能理解浩当时的拒绝。倒是在经历这事以后,家里人再也不催着她结婚了。
欣怡仍做着以前的工作,收入颇丰,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两处房子,对爱情,不拒绝也不刻意追求。
一天,我听好友讲了欣怡的故事,她说这是她遇见的女孩中,对感情最节制也最有分寸感的一位。
而我想到这个故事,眼前就闪出这样一幕:一个刚刚失恋、失魂落魄的女孩,空着肚子赶了20个小时的火车。这20个小时,也许不够埋葬她的委屈和失望,直到强烈的饥饿感充当现实的使者横在受伤的心面前,她顿悟了——也许我也不是很爱他,否则为什么一碗面就能令我快乐起来?
生活往往就是如此,爱使人快乐,但那不是唯一的快乐,正如它不是唯一的苦痛一样。
生活的坑都是自己挖的
看起来,一个人把自己交给痛苦,比交给快乐更容易一些。
譬如,听别人讲话,听到最后,耳朵里只会记住两类话:最愿意听的和最不愿意听的。然后,喜欢听的未必化成快乐,但不喜欢听的一定化成了痛苦,其他的都化成了风。
有时候,风都早已刮过去了,一颗心,却还在一片无关痛痒的云彩里下着雨。
人的选择性就是这么顽固,顽固得近乎荒唐。也就是说,你本可以云淡风轻地活,然而,却无缘无故地受了伤。是的,有些伤害是来找你的,而有些伤害是你找来的。
好多人强大的想象力,都用在了自戕上。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,稍加勾连,就能安排在自己身上。那边还没风声鹤唳呢,这边早已四面楚歌了。就这样,在近乎扭曲的想象力中,完成自戕,又在自戕中,进一步壮大着自我想象力的扭曲。
这个世界上没有愿意自讨苦吃的人,但多少人每天都在自讨苦吃。也就是说,你还没与这个世界真刀真枪干呢,就先在心底里,与另外一个自己厮打到不可开交。
好多时候,是自己把自己折腾累了,自己把自己纠缠烦了,然后,这个自己挣脱不开另一个自己。
坑其实是自己挖的。光阴的泥淖里,多少人,都自己逗着自己玩。
如果生活没有对你曾经犯下的错误做出惩罚,你要告诉自己,这就是宽恕。
但不要因此而得寸进尺。或者说,你不能因此而欺负生活,给脸不要脸。生活不想以此纵容谁,只是想让所有人明白,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。
有的人,等到生活开始惩罚自己了,才想起后悔。这样的忏悔,不值得原谅。从无意犯错到故意犯错,应该推敲的,不是人生,而是人性。为恶的人性辩护,本质上就是怙恶不悛。
也不要把这一切都推给命运。既然所有的结局,开始就已经料到。所有的惩罚,都是水到渠成的铺垫。不要让命运为你的贪婪买单。在欲海里浮沉的人,个个都是亡命徒。为欲望亡命,是已经注定了的结局。
这个世界,有侥幸。但不宽恕侥幸。不要把自己一步一步拖到付出代价的境地。生活中一切的罪与非罪,罚与非罚,良心会有知,光阴会有知,天地会有知。
不去欺负生活,生活自会安妥地待你。清白干净的灵魂,特征只有一个:无愧过往,不畏将来。
这个世界上,有两种人难败:太要脸的人和太不要脸的人。太不要脸的人是不怕败,太要脸的人是不敢败。
虚荣的人属于后一种。
由于太在乎面子,虚荣的人终会被虚荣所伤,但无论多深的伤,虚荣又是最好的创可贴。因为,于他们来说,一方面怕别人看不到自己的好;另一方面又怕别人看穿自己的不好。
于是,虚荣很好地炫耀了自己,也妥善地遮掩了自己。
只要能在人前风光,心底受多深的伤也愿捱着。虚荣的人,一辈子,为了这点荣光和浮华,透支着人生太多太多的东西。然而没办法,相比于取悦自己,他们更愿意取悦世界。因为,只有在别人的艳羡和嫉妒里,他们才能找到自己,才会找到快乐。
在虚荣的路上走多远,就会有多伤。虚荣的人不敢转身,因为一转身,就会看见千疮百孔的心底,以及委屈受尽的苍凉。
虚荣是虚荣者一生的宿命。他们只能往前走,也必须往前走。虚荣的人,是这个世界走丢的孩子,喊也喊不回来。
即便互相亏欠,也别再藕断丝连
周六打着给B小姐庆生的名义,约上她们两人一起吃饭。席间B小姐提起了李先生回国的消息,然后问女神:“他不是约你吃饭吗?”
女神低低得“嗯”了一声,然后说:“不想去。”
我问她为什么。
女神喝了一口饮料,苦笑着说:“我怕我看到他的脸,眼泪就会止不住得掉下来。”
女神和李先生都是彼此的初恋,同一个初中和高中。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女神经常会提起李先生的名字,说他的种种故事。明明毫无笑点的一件事,女神说起来也会笑得上气不接下气,留下我和B小姐面面相觑。现在想起来,大概是从那时候起,女神和李先生开始对彼此暗生情愫的吧。
后来某次逼问,女神终于坦诚了她和李先生走在了一起,是李先生表的白。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,感觉好像就在昨天,可是翻翻日历,却竟然已经过去了七年。在相爱的四年里,他们一直都很甜蜜,女神娇娇嗲嗲,李先生百般呵护,从未听过他们吵过架。
直到李先生出国的前夕,女神突然提了分手。往后的时间里,女神从没有说过分手的缘由,像是某种奇怪的默契,她和李先生对于分开这件事保持了共同的缄默。她也不在我和B小姐面前哭,也没有颓丧,只是有一段时间,会突然陷入了久久的无言,就好像突然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。
没有电影里那种分开后的撕心裂肺肝肠寸断,或是有,只是旁人看不到。女神和李先生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,偶尔聊天,问候近况。比起那些分手以后就对前任破口大骂的男女,他们的行为,总让我想起那句“亲人不出恶言”。分开以后至今的三年里,女神和李先生在不同的国家生活,却都保持着单身。这几年里也不是没有人追女神,可是她总是笑笑,然后再也没下文。
昨晚我问女神:“你还喜欢他吗?”
女神说:“我不知道。”
我说:“你们那么久都没有断了联系,没办法复合,至少还是朋友。”
女神没有回复。
良久,她才发来一句:“互相喜欢的人,是做不了朋友的。”
你看,她什么都知道,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。不愿意承认哪怕还喜欢,也不想再回头。
昨天在家删以前的一些微博。看到2012年的时候,@朋友,那时候他的ID还是“S爱T”一类,S是朋友的名字,而T则是他当时的女友。T姑娘很美,毕业以后去了某国求学。有一次她对我说,某个曾经她和S共同的朋友对她表白,她拒绝了。也不是那个男生不好,而是T一看到那个男生,脑海里浮现的都是S的脸。
T和S是2011年的光棍节在一起的。
他们来自同一个城市,又一起到了魔都求学。我们都曾觉得这是一对天作之合。可是T的父母却反对他们在一起,据T说,是觉得S还不够稳重吧。由于父母的高压政策,在学校的时候反而成了他们最自由的时光,而每逢放假,就只好发短信互诉衷肠。时间久了,总有些不愉快,S和T的争执越来越多,温情也越来越少,不知为何,见面总是不愿意好好得说一说相爱,而学会了用语言互相伤害。
可怕的是,两个人越是亲近,就越知道用怎样的方式才会让对方溃不成军,渐渐S来找我们喝酒的次数从一个月一次,变成了一周一次。S饮至深夜,手机的屏幕也一直黯淡无光,T再也不会深夜发消息,絮絮叨叨得让他早点休息。
两个人之间变得冷漠连旁人都感觉得到,可是他们似乎是跟对方在置气,谁都不愿意主动提分手。又或者他们都相信一切都有挽回的那一刻,只是伤害太多,不懂从何做起。曾以为这种僵持会一直延续。可是某天,忽然的,就断了。不知道是谁稍稍用了一把力,打破了角力的平衡,只知道后来他们又各自有了对象,又再次分手,也刻意互相躲避,不再相见。
2014年年初的时候,S和T在某次聚会上重逢,身边的朋友们坏笑着让他们坐在了一起,怂恿S一杯杯得喝酒。S喝得满脸通红,拉住了T的手,很认真得说:“我一直都没有忘了你,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?”
T拼命点头,潸然泪下。
可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。没有争吵没有伤害,只是对彼此留下了一句祝你幸福。
这一次,是真的结束了吧。
我相信女神和李先生,S和T都彼此真的相爱过。写完S和T这一部分的时候,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女神不愿意去和李先生见面。有些记忆里的人,原来是真的不能再相见的。不论你还好,或者不像以前那么好了,那些涌上来的情绪都足以把一个人淹没,多到让你分不清,你究竟是想离开还是仍然还爱。
那个人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熟悉,却又变得那样陌生。
我曾经和他唇齿相依,如今却相隔两岸。
这世上总有那么多对分开的人,彼此认真得对待过,最后也无奈得说了再见。当初让你提分手的理由,总有一天还会困扰你的复合。是,他曾走进过你的心里,也再不会离开。可是那有什么要紧的呢,他从光明的繁花盛开处,走到了那个偏僻的小小的黑木屋。
你不会刻意去想起你曾爱过,也不会特意去抹去这个人。
他就像那一根你曾经撞过的电线杆。或许你还记得撞了一下的那种疼,可是却再也没必要去撞第二次了。而再久一点,疼也会被你忘记。只留电线杆仍然矗立,不来不去,无声无息。
我很欣赏女神的不见,也赞叹T和S最后一次分手后的再也不见。
与前任的告别,是对今后那个陪伴你的人的尊重。
即便互相亏欠,也别再藕断丝连。
年轻人,不要随便否定自己的价值
在这个城市,总有那么一些人,习惯否定自己。充满了挫败,抑郁。看不到自己的价值,这也不好,那也不好。然后羡慕着别人的好或者幻想着一种理想的状态发呆。
我曾经是其中一个。在北京挣扎,找不到方向,找不到出路,更找不到价值。每月领着两千块的薪水,不敢随便请人吃饭甚至不敢轻易吃肉,更不敢去谈朋友。在理想面前,所有的现实生活都很奢侈。更可怕的是,没有阅历没有能力没有任何积累,而最让自己难以接受的,则是性格懒散不思进取不够努力,许久来却没有一丝改变的迹象。要财没有要才也没有,甚至连长相都没有,几年下来,依然在挣扎。然后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,不知道活着这么痛苦有什么意义,然后用沉沦来安慰自己。只有在偶尔回到家的时候,和朋友谈论起,在哪工作,北京。不知道是一股自豪还是自卑感从心底升起。只有听朋友谈论起,你这不错那不错的时候,才开始半信半疑。只有当朋友用羡慕的眼神列举出一大串优点的时候,才开始反思,为什么,我要这么否定自己呢。
当我开始注意的时候,就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,不断去否定自己。
他们否定自己的理由跟我大径相同:年纪大了依然被剩,自己找不到对象觉得要孤独终老;无才无貌平凡到不被人注意到,觉得这就是生活的悲剧;领着微薄的薪水,痛恨着自己没有能力;拼命坚持着却找不到方向弄丢了理想,觉得再无出头之日;性格懒散拖延成性,能力不济毫不上进,觉得自己活该生活凄惨。总之结局都一样,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一无是处,没有未来没有伴侣,找不到活着的感觉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。
可是我又很好奇,既然自己这么差,一直都这么差,又是什么让你坚持活到了现在,还活得好好的。是不是真的因为自己太差,就这么否定了自己。很显然不是。和比尔?盖茨比,我们都太穷。和姚明比,我们都太矮。和玛丽莲?梦露比,我们身材真的太差。和周润发比,我们又有些丑。我们总能发现有人有地方比我们好,那是不是我们就要否定自己。
你说,他们都是名人,你并不奢望达到那个地步,你只是想有个正常的能力。可是你告诉我,界限在哪里。和吃不上饭的孩子比,你又太优越,和重病在床时的人比,你又太健康,和被大火毁容的女孩比,你又太美丽。和在工地上挥汗的伯伯比,你在办公室又太舒适。那么这个正常或者比较的标准在哪里。
这个世界上,总有些人的有些方面比我们优秀,让我们惭愧难当。我们想成为那样,却没有做到,然后挫败,然后否定自己。可是你又是否知道他的痛苦。我们羡慕那些年轻有为的咨询师,却看不到他成长的历程中父母早年离异自己饱受沧桑,他只想象我们一样有个正常的家。我们羡慕那个有钱的孩子继承了父亲遗产,可是他只想用所有的钱换回父亲的一年,羡慕我们父母虽穷但是依然健康。我们羡慕那个在单位叱咤风云的女领导,可是她年近四十依然跨不上红地毯,她羡慕我们活得平凡但家庭和睦。我们羡慕的很多人都在羡慕着我们。
听起来像是每个人都有优缺点,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。我们要做的仅仅是不要比较而已。我们不可能成为那个完美的人,在所有方面都是最优秀。有些人有些方面会比我们优秀,但是这些人同样羡慕我们的一些其他方面。羡慕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他们却拥有不起的东西。
既然没有完美的人,那我们只要多看看自己的优点和拥有的地方就好了,就容易感觉到价值了。我们都是半杯水,看你是看到空的部分,还是看到有的部分。
我们拥有太多资源被我们所忽略,以至于我们常常挖掘自己的优点或价值的时候,也难以找到。
我们能工作在北京,却感觉不到价值。我们享受着办公室的空调,感觉不到价值。我们健健康康着,却感觉不到价值。我们父母曾好好爱我们,我们感觉不到价值。我们还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奋斗着,我们感觉不到价值。我们在北京租得起房子,我们感觉不到价值。我们能吃饱饭,我们感觉不到价值。
可是当我们换一个环境的时候,又感觉两样。当我们回到家,带着北京的特产给亲戚朋友,我们享受着那些羡慕在北京工作的眼光;当我们到孤儿院去救济献爱心的时候,我们又感恩着父母给的幸福;当我们和给家里装修的工人一起用餐的时候,又怀念起单位的空调温度;当我们去医院探视的时候,又庆幸着自己的健康;当我们和刚失业的朋友聊天的时候,又觉得自己能领到两千块而沾沾自喜。
同样是那些让你感觉不好的东西,又会让你感觉很好。价值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,同样是我们拥有的特质,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很好有时候又让我们感觉很差,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却没有变。那是不是环境变了,我们的价值感就变了。也就是环境控制了我们的价值感。
我们的价值到底建立在哪里之上。
很多年前,当我还没有开始研习心理学的时候,我听说,幸福是由你的邻居决定的。当你拥有了你的邻居没有的东西的时候,你就会感觉到价值,感觉到幸福。好可悲的思想,我们自己的价值感,居然要被环境所控制。我们把价值建立在环境之上。
有时候,别人夸我们,说了我们很多好,我们就觉得得意,喜笑颜开。别人说我们不好,说了我们很多缺点,我们就觉得难过,自己哪都不好。又常常把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评判之上。如果从事的是公务员,有的人羡慕我们的工作有的人则说我们安于现状。如果我们吃饭吃两盘肉,有的人说我们浪费有的人则说我们爱自己。如果我们赚到很多钱,有的人说我们能干有的人说我们精神匮乏有什么用。如果我们考试考了高分,有的人说我们学习好有的人说我们是书呆子。我们听到不同话的时候,感受就会不一样。
我们是否要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环境之上,那么当我们失去环境独处的时候,我们的价值感要从何而来。我们是不是要将价值感建立在他人之上,那当不同的人说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。
没有一样特质是好或者是坏,只是我们身上的一样特质,只是我们用了褒贬的形容词来形容。但当我们把他还原,他依然只是我们拥有的特质。倔强其实就是坚持,讨好其实就是爱心,指责其实是力量。年近三旬是成熟美,长得太平凡则是安全。防御是因为保护自己。如果我们退去了比较和评判,那只是我们身上的特质而已。无所谓好坏。
我们都是半杯水,没有人会一满杯。有空的部分,也有有的部分。看到什么,则就有什么。